「最後一次問妳。確定?」
「確定。」
「剪頭髮不是試衣服,剪下來的頭髮穿不回去啊?」
「……嗯。」
髮型師聳肩,舉起手上那把磨得鋒利的剪刀,將她脖頸邊上一縷鬢髮架在利刃中間。
「等等!果然還是……」
咔嚓一響,兩柄刀刃相交,剪掉了她耳畔的空氣。
「請掙扎。」他將剪刀收回腰際的布套。「這絕對是一件值得掙扎的事。」
她嘴唇翕動,但話音被鄰座的風筒聲掩蓋。這家 SALON 只有四個坐位,由一對 GAY COUPLE 經營。正因為小,只要風筒一開,甚麼對話都要等頭髮吹好再說。
這段時間,髮型師拿掃把清理地上的一些碎髮。
風筒聲終止後,她問道:「像我這種年紀還留長髮的客人有幾成?」
「一成又怎樣兩成又怎樣?」
「後生細女呢?」
「……超過一半吧。」
「不就是。」她說。「所以 OFFICE 那些人說我四五十歲還在發姣,不是沒有道理。」
「發姣歸發姣,貪靚只是貪靚。」
「但從某個角度而言,她們這樣看我也是無可厚非。歸根究柢,年紀大,頭髮就會變弱變薄,從打理或者美觀的角度看都不再適合留長。我有沒有說錯?」
「有沒有說錯……」他摸著下巴的鬍渣,拈起她的一縷長髮,在靠近髮梢處朝上折,於是髮尾便整齊而順滑地翹起,像一束新鮮採摘的花。
她又道:「網上是這樣說的。」
「那些文章錯的不是內容,而是前設。它假設所有人的髮質都是同一個樣。熟女留長是比較少,但不是沒有。妳看。」髮型師朝天花板指了指。
「JANE BIRKIN 就是留長髮。這首歌叫甚麼?GER TAY MEE……」
她嘖了一聲:「JE T’AIME… MOI NON PLUS。」
「對。發音差不多。」
「不對。這完全沒有參考價值。JANE BIRKIN 唱這首歌時幾歲?我現在又幾歲?」
「我記得她是帶著長髮進棺材的啊。」他打開手機想要確認。
「不用查了。」她說。「就算是這樣,她是 JANE BIRKIN,就算把頭髮全剪了貼在屁股上也會有人讚漂亮。」
髮型師後退一步,故作審視她屁股。
「喂!」她佯怒。「性騷擾。」
他改為看她的臉,然後搖頭。
「我不覺得妳比 JANE BIRKIN 差很多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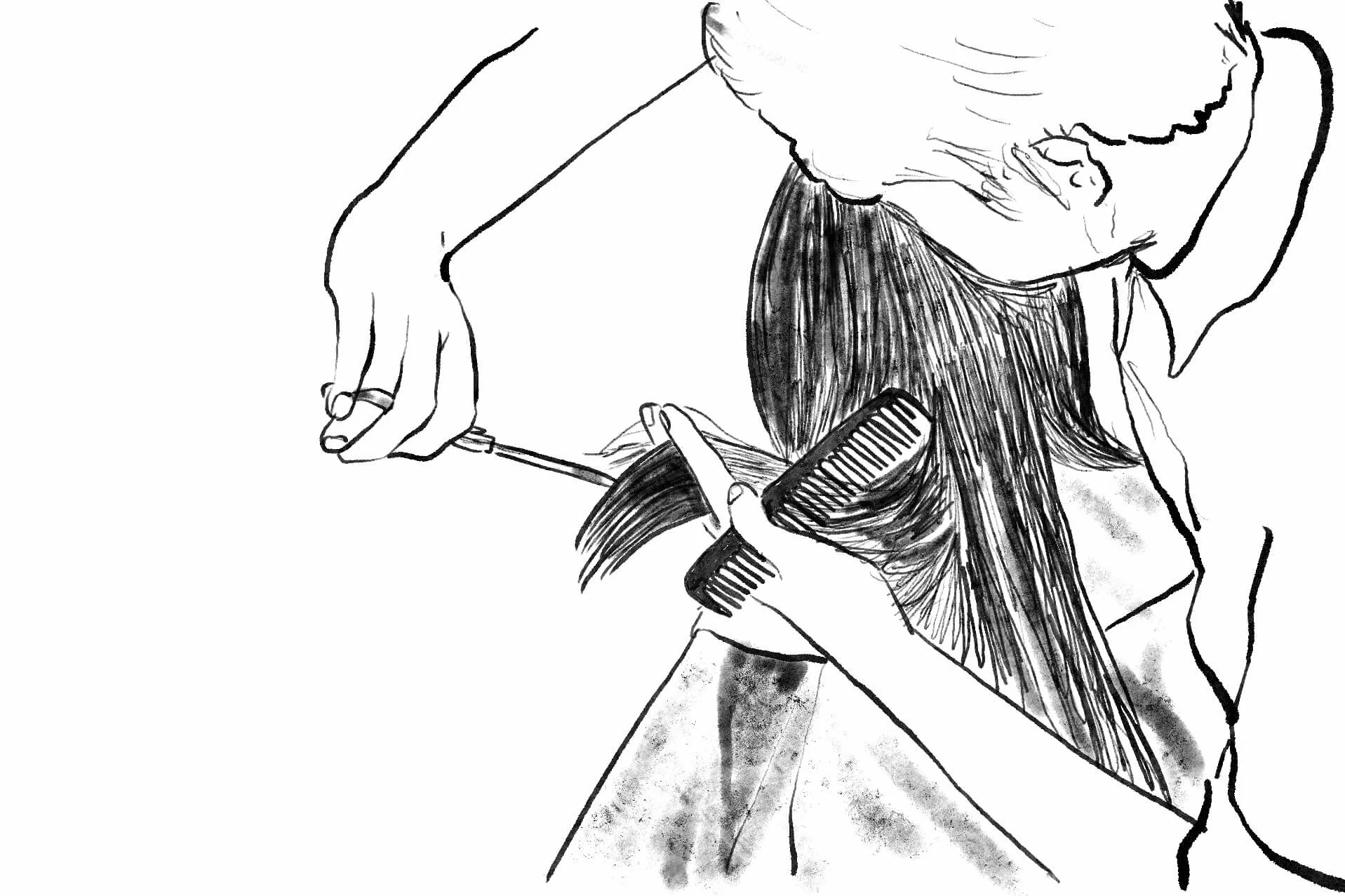
雖說口甜舌滑是理髮專業的一環,但我也認同這位髮型師說的是實話。儘管這女人確實不年輕,但眼角的魚尾紋和些須鬆馳的臉頰並沒消減她的魅力,反而讓她散發出一種沉實的韻味,像有了內容的威士忌。
「我有說自己醜麼?」
髮型師笑。「要不要把頭髮貼在屁股上試試看?」
「我的意思是,她是名人巨星,而我是平民百姓。她做甚麼都是風格,而我是瘋格,瘋婆婆的瘋。」
「別人怎麼想跟妳有甚麼關係。頭是妳自己的,怎剪是妳的自由。」
她不滿意地擺手。「頭是我的沒錯,但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不會看到我的頭,那也是我。」
「哎呀,別管那些人不就好了?講是講非是地球人的習性,實際上,又有誰真正在乎妳的頭髮是長是短,地球上那麼多人,每個人都有一個頭——」
「地球人當然有頭,民主剛果的人也有頭沒錯,可他們的頭跟我有甚麼關係?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我知道的,只是在 OFFICE,那些女人和男人會用看白雪公主的巫婆的眼神,盯著我,煞有介事,交頭接耳。你說不必在意別人目光,你當然可以這樣說,被嘲笑的又不是你。你頂多表達個三秒鐘的同情,發表個三分鐘的高論,然後又可以繼續去弄別人的頭了,沒所謂。不是嗎?」
一口氣說完後她才注意到自己的聲量堪比剛才的風筒,於是轉而小聲說「抱歉」。
髮型師倒沒生氣,只是在一陣短暫的沉默過後道:「我剪妳的頭已經剪了十年。」
「……嗯。」
「妳頭型方,就是不適合短髮啊。對,年紀大髮質是會變弱,這是事實,但頭髮長短是選擇。只要勤點打理、洗髮水不要用太刺激性的、吹頭不要用高熱、盡可能不要用捲發器,那就不會有太大問題。」
她點頭。
「為免妳又說我無所謂,長髮妳留,保養我做,又如何?我是真的建議妳不要剪。所謂漂亮就是求開心。妳想想,待會行出這家店,是長頭髮比較開心,還是短頭髮比較開心?勇敢一點,對自己有信心一點,好不好?」
「你下個 APPOINTMENT 甚麼時候?讓我多考慮……五分鐘?」
「我叫下個客遲五分鐘到。」
他去打電話,她坐著沉思。披著剪髮袍一動不動的她就好像一座未完成的雕塑。創作主旨可能是表現某種人類生存狀態的天人交戰。我不敢說自己看得通,甚至不敢說能夠體諒,畢竟我不過是個恰好坐她鄰座的閒人,而且是個男人。
不過我可以清楚這裡面確實有天人交戰沒錯。畢竟,我也已經是要染髮的年紀了。
注意到我透過鏡中的倒影看她,她微微一笑。「抱歉,是不是吵到你?」
「沒事,反正沒事。」
「你每次染髮都不是看書便是小睡。」說完又突然像意識到甚麼地搖頭。「不是刻意注意的,碰巧而已。」
「這邊也是。」我說。
「甚麼?」
髮型師回來了。
「最後答案?」他問。
她不再看我,也不看髮型師,而是看鏡中的自己,深深吸一口氣。「我可以懂為甚麼你說短髮不適合我。我也覺得不適合我。」
髮型師抿起嘴,待她繼續說下去。
「不過,我的目光終究只是我的目光,你的目光也不過是你的目光而已。我不否認你那是專業的目光,但專業的目光並不是世界的目光,也不能改變世界;一如我,也不能夠。這是事實。」
「而不見選擇。」髮型師說。
「確實如此。但是,我也很清楚自己想選擇的,就算聽起來多麼庸碌都好,並不是一句『與我無關』就可以跟世界割裂的。」
他吁一口氣,蹲下來,手肘支在膝蓋,托著腮看進她的雙眼。她也看進他。他們之間也許交換了三分鐘的無言無語,然後髮型師站起,伸手,在她右肩上方用兩根手指夾著她的頭髮。
「確定?」
「確定。」她一頓,說:「抱歉,沒聽你話。」
「啊?我覺得妳有。」
「甚麼?」
「要勇敢,要對自己有信心。」
她瞇起兩眼。儘管這令她的皺紋變得更加明顯,但那神情卻讓人想到小女孩在某種舞台上得到嘉獎。
「我一直都是個自信又勇敢的女人。」
「『不好看』也有『極不好看』和『一點點不好看但完全可以接受』之分,我們以後者為目標吧。」
「當然。」她說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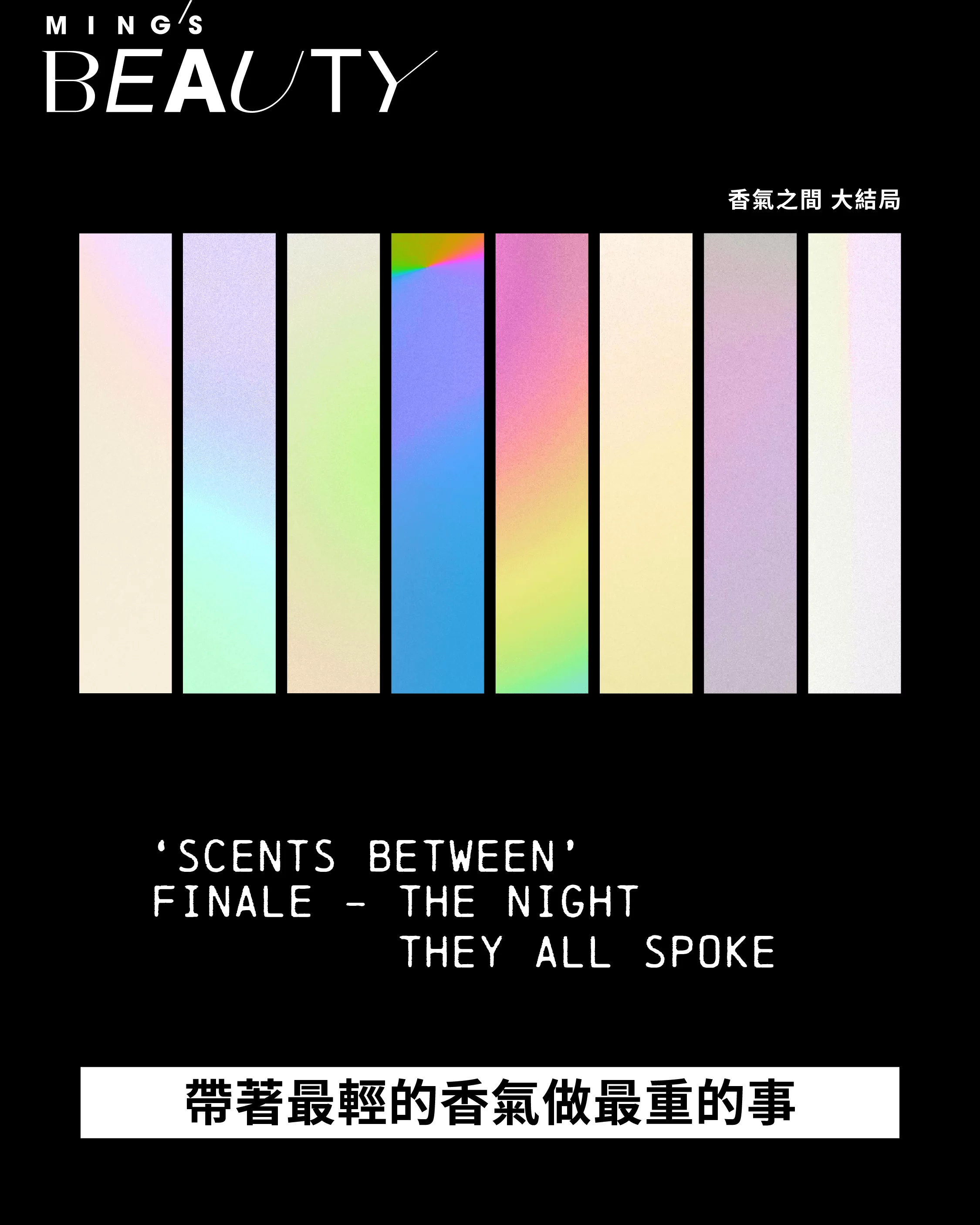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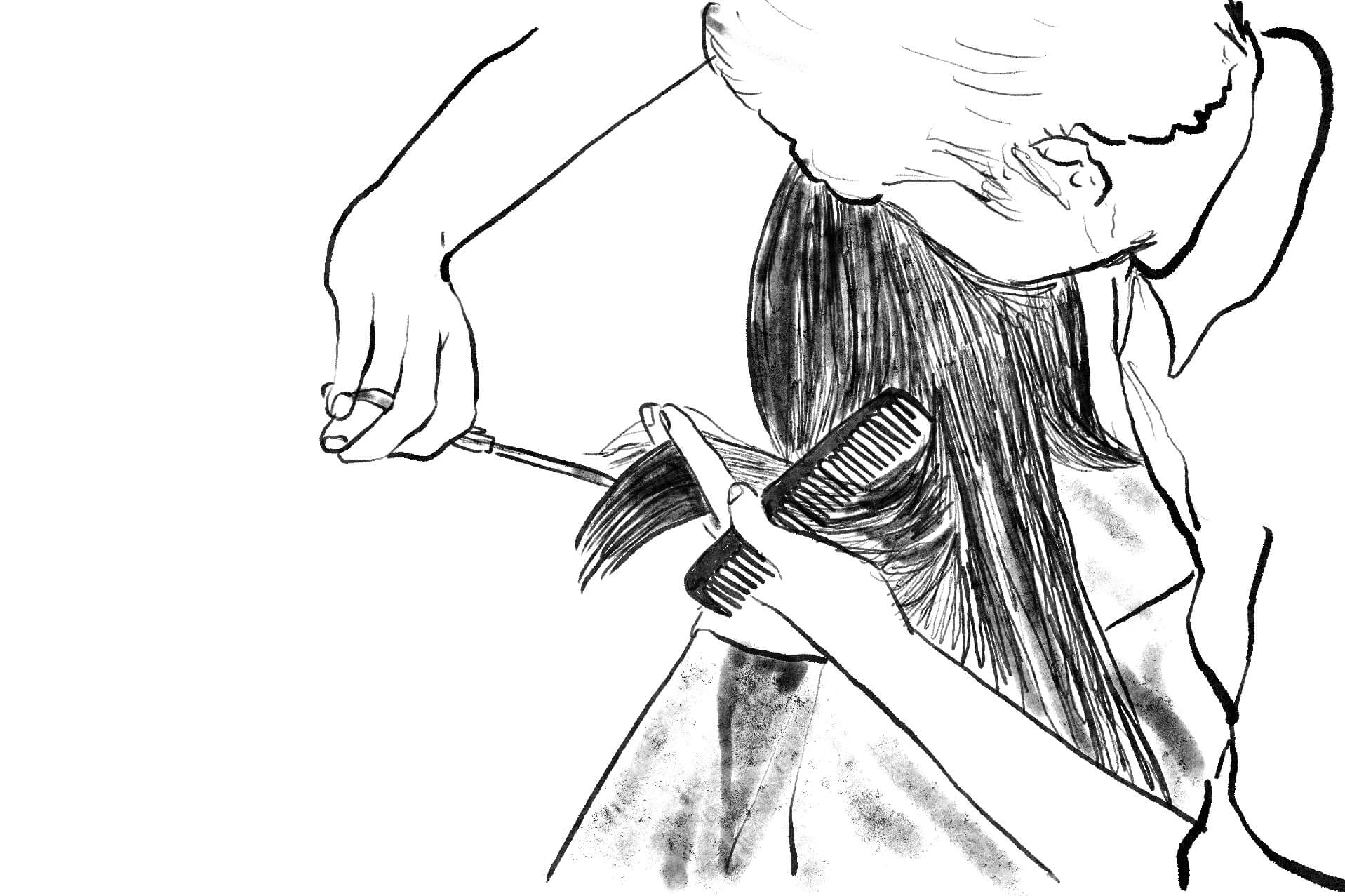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