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可能是因為昨天看了遲定芳為《何式性望愛》寫的書評,也可能是剛聽完Serrini的那首《你不想再跟我看戲》,令我突然想起我的前度。在很長很長的日子,沒有這樣想念他,當然偶然會想起,卻沒有什麼思念,今早卻分明是想念。很想走到他面前跟他說:「我老了!怎會這樣?」還有:「我們怎麼會搞成這樣?」然後大哭一場。
在我此刻的想像中,他依然是有最好安慰我的說話,也不會因為我傷害過他什麼而在我伸出手要拖他一下的時候撇開我。大家都經歷過這麼多,他會明白我的感觸,一定會說出好聽的話,演好我們相遇三十多年後的這一幕。然後呢?大概沒有然後。以後即使在演唱會後台又再相遇,我們還是會裝作沒有見到大家,這就是我們的結局。「也許我會忘記,也許會更想你,也許已沒有也許。」真愛和真普選,都這麼困難。我們在開始不久已經放棄了。
最近去過soul reading,據說是new age的一種「算命」吧。替我「算命」的人說她代我的靈魂跟我說:「這不是愛情的問題,是你的自尊心嚴重受創。」我的自尊心怎會這麼重?怎會這麼容易受傷又好不起來?今天為什麼這麼軟弱?我的自尊心又來搞我嗎?7月1日之後,我從一個tenured的full professor變成了一個contract staff,開始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合約,表面上分別不大,但爭取這個延期退休的過程,讓我受到人生中前所未有的歧視,就像是去乞求一份工。大家得到五年,我只得到零,經過呼天搶地的投訴才得到平反,俾你兩年。這種委屈,在法國學習現代舞的時候會覺得好一點,回到香港又頂不住。然後又看到黎青龍教授的訪問,他是全球肝病權威,65 歳之後,自己找贊助人捐款,才能保住自己的職位。70 歳了,大學要逼他轉為「兼職」,怎會受得了?
同事Professor Timothy O’Leary剛剛離開港大去New South Wales!他說:「因為在澳洲做教授是沒有退休年齡的。」在北美也沒有。還有,一位美國教授正式退休之後,她還可以保留自己的辦公室三年。聽到我們這裏60歲的教授受到的對待,他們都覺得港大是“ruthless”!
我所認識的香港大學,絕不會承認這是年齡歧視,即使覺得,也絕不會帶頭改變香港的歧視問題,這不是大學的priority,他們認為最重要是增強競爭力。但競爭力又是什麼呢?趕走年過60卻仍很有productivity的權威教授,根本是與「增強競爭力」相反的做法啊。這種無情正正是大學想假裝並不old seafood:「看,我們不停吸納新力軍,沒有讓大學變成老人院。」但背後其實正正是一套old seafood的僵化制度,沒有讓制度可以更靈活又更人性化地對待各個年齡、層級的學者,不去刻薄甚或剝削學者的教研追求和理想。在這樣的社會,我怎麼可以熬到70歲?我還可以打晒煲呔襯套黃色西裝,告訴大家,我不但是一個堂堂正正的正教授,也是一個好sharp的教授嗎?
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事情會令我vulnerable到要想起我的前度,這兩種經驗是相關的嗎?一個傷口和另一個傷口會連接起來嗎?還是其實是同一個傷口?如果我真的能夠走到他的面前哭起來,我的自尊心就會恢復一點嗎?我就能夠面對大學的無情嗎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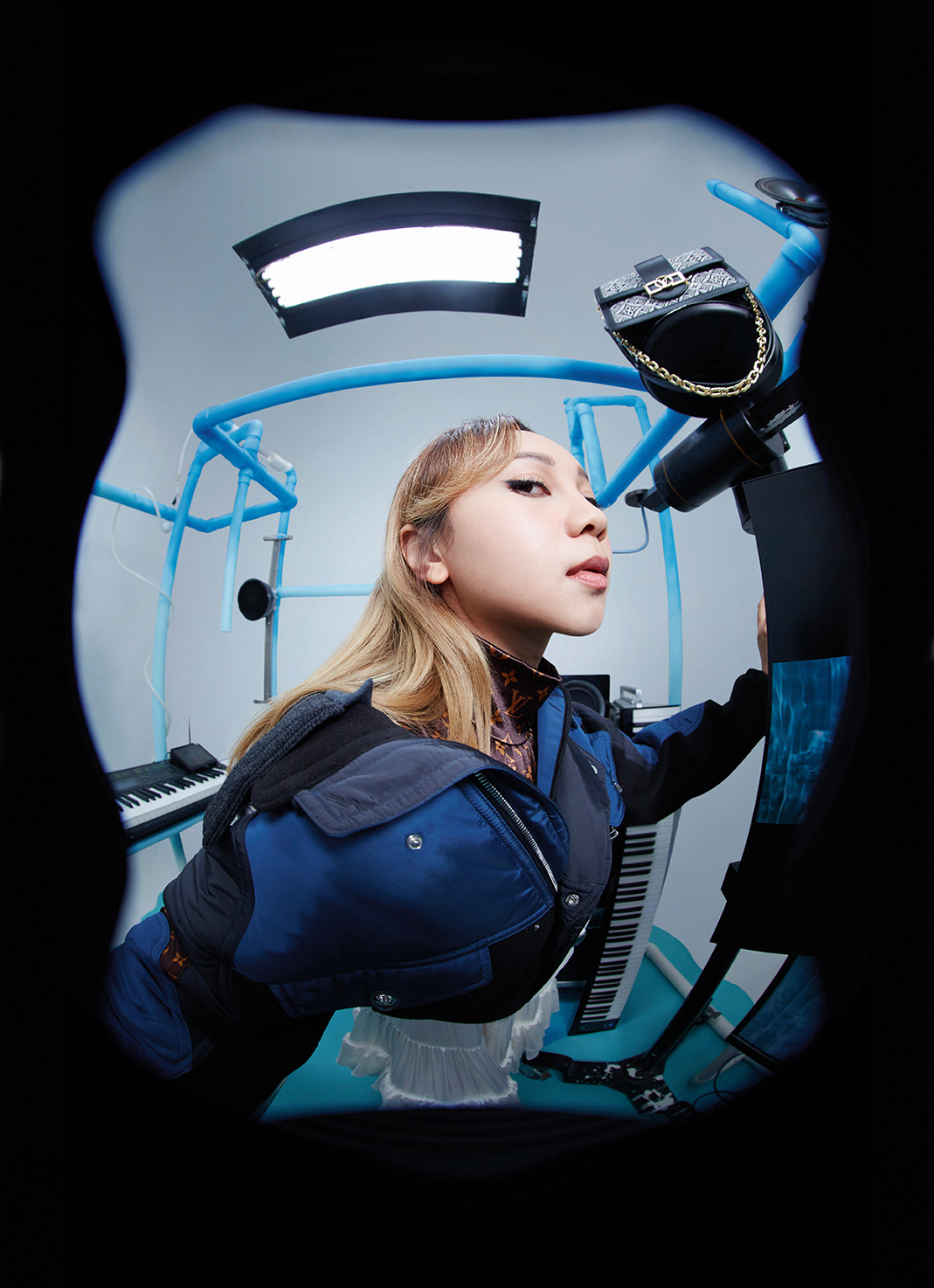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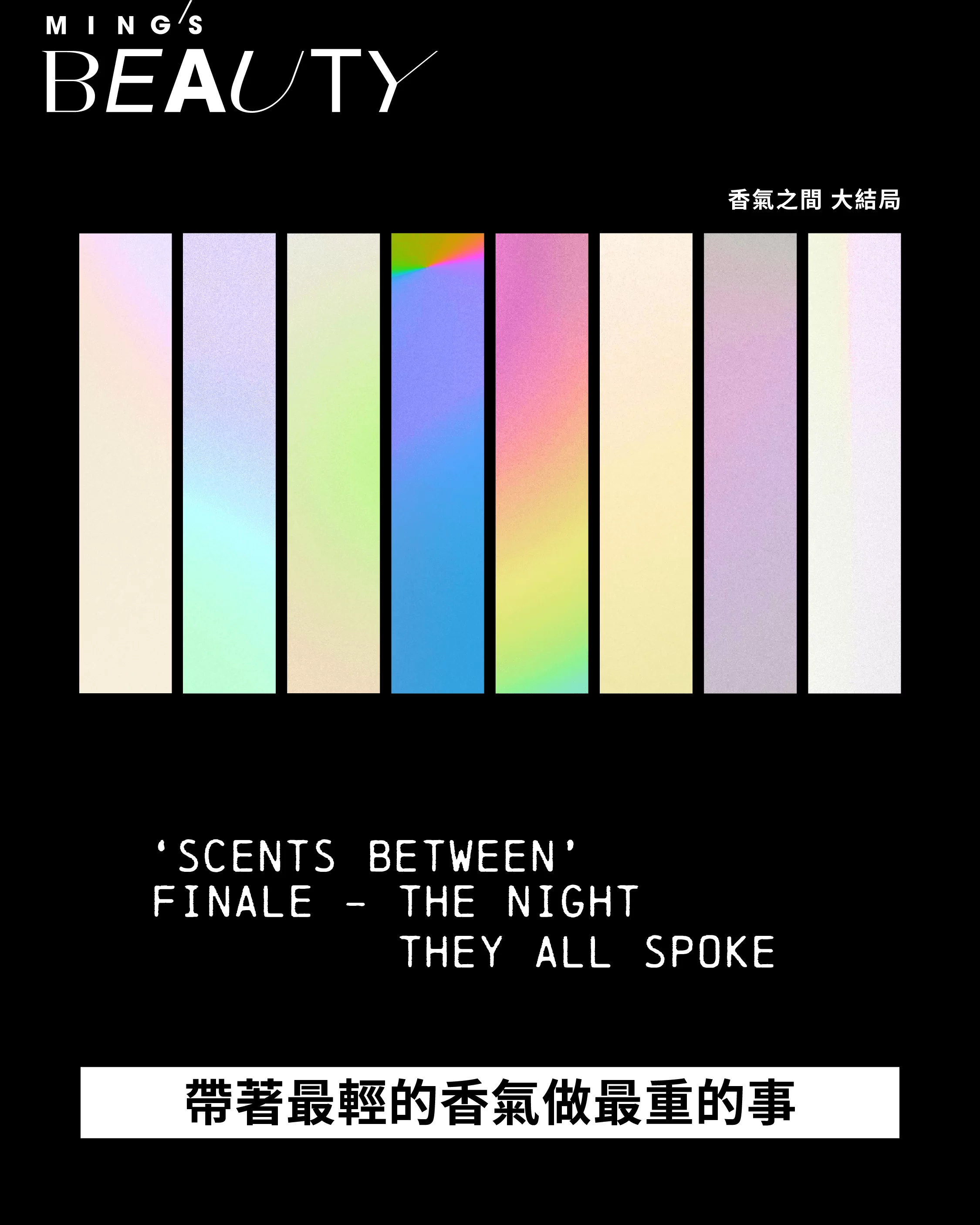





Comments